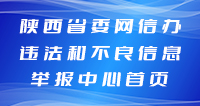编者按:本文作者刘小龙为文学硕士,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。该文刊发于11月22日《书法导报》后,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评价。
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、中国职工书画院院长兼秘书长王登科认为:该文史料翔实,爬梳钩沉,论据充分,加之其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写作方法,向读者充分展示出了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学术理想。论文结论固然重要,但“辨章”与“考镜”过程同样重要,它是学术研究中理性之于人生的美好馈赠。
著名艺术家刘若望说:刘小龙的辨伪之文,引经据典,言必有据,从《非草书》所涉时代社会特征、人文特征、政治规则、文化风尚等方面加以论证,使得该文论点更为可信,足见作者学养深厚,治学严谨。这正是所有艺术家、艺术史家乃至艺术评论者应有的学术素养和应持的学术精神。
国家二级美术师、艺术史学家、书法理论家朱中原认为:作者对前人相关论述及史料皆持审慎态度,对前人成说不盲目采信。作为一家之新论,不失为一篇非常具有史学价值之书法文献学论文!
榆林学院文学院院长贺智利认为:该文多以正史为据,从文献出发,由文献自证,部分观点又采用了吕思勉、马宗霍、唐兰等当代文史大家著作。立论可靠,论据确凿,论证充分,有理有据,对《非草书》的讹错做了全方位辨析,令人信服。赵壹《非草书》在书学史上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,该辨伪文章在《书法导报》“书法理论”专版发表,或许对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汉晋书法史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。
引言
唐人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收《非草书》一文,署名“后汉赵壹”,后世广为征引,以其为据论断汉晋书法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:把今草之成熟,由东晋“二王”提前到东汉张芝。有的则从文艺理论及文学思想史角度出发,认为《非草书》所反映出的才性论,开魏晋文学批评理论先声。但对《非草书》本身的真伪研究极少。虽有论者质疑《非草书》,然多囿于细枝末节,未能提出足够证据令人折服。
该文在辑入《法书要录》前,仅有张怀瓘《书断》“赵壹有贬草之论”一语。张氏论书多出臆断,其叙隶、章、草之源流,强造统系特好断章取义。征引史例,或擅改史文合其私意,或罔顾史籍骋其臆说,误解“草”“史书”“善书”古籍术语本义等,致其论述汉晋书史错谬不少。
检阅汉唐之际史籍,结合赵壹本传、汉晋士风、“上比下方”之词先后出处,尤其是通过分析文本所持论据的逻辑性、所引时事的真实性,以及梳理才性论的历史流变等,可以判断《非草书》并非出自东汉赵壹。
一、《非草书》必是基于已有论草篇什而发
从《非草书》“故其赞曰‘临事从宜’”及“第以此篇 研思锐精”二语来看,即可推知该文必是基于某一特定论草篇什而发。否则,“其赞”“此篇”指代不明,无法理解。如果真出自赵壹之手,其可依据之文,只能是他生前可见的论草之作。赵壹大约死于188年(赵逵夫先生在《文学遗产》发赵壹考证文章,卒年取其下限188年),该年之前的论草文章,仅有崔瑗《草书势》。崔之“临时从宜”与“临事从宜”一字之差,可视为同义语。但结合二者上下文来看,则大相径庭。崔以“临时从宜”强调作草之际,点画安置,方圆笔势,了无定法。而《非草书》则以“临事从宜”解释篆隶到草的书体演变,乃出权宜。赵壹不当征引似是而非之“赞”以论述草书本末?此外,《隶势赞》有“随事从宜”之语,然此也与崔瑗之词用意相同,与《非草书》“临事从宜”则天壤之别。索靖《草书状》以“随时之宜”来论述科斗鸟篆到隶草,乃是权变的结果,与《非草书》“临事从宜”用意相通。且《隶势赞》“蠲彼繁文,从此简易”及索靖“损之隶草,以崇简易”,与《非草书》“故为隶草,趋急速耳,示简易之旨”何其相似!但赵壹不可能预知西晋论草之作。
此外,《非草书》以气血筋骨、疏密巧拙、迟速好丑等术语批驳学草之人,也非赵壹所能发此宏论。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的才性论,固然与《庄子》轮扁斫轮心手之论、《淮南子》工匠瞽师父子兄弟之议、桓谭《新论》人心独晓之说,以及王充《论衡》所言才性清浊等不无关系。但学术思想之传承发扬,绝非朝夕之事。兹以桓谭为例说明这一问题。桓氏身居郎位,尚需向班嗣借《庄子》,而班嗣之书源自朝廷赐予,以此可知古籍甚不易得。桓谭论“材”之所以能体现庄子思想,与其师友扬雄、刘歆不无关系。王充得以承继前人,也与他师事班彪关系甚大。但我们不能以桓、王前后承继之事来推演赵壹,因为赵壹不具备继承王充学术思想的客观条件。史载“王充所作《论衡》,中土未有传者,蔡邕入吴始得之,恒秘玩以为谈助。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,又得其书……果以《论衡》之益,由是遂见传焉”。
蔡邕于光和二年(179)遇赦,南下吴会流寓十二年,中平六年(189)返洛阳,初平元年(190)“从献帝迁都长安”,两年后被害。至于王朗为会稽太守,则更是蔡邕身后之事。此时赵壹已死,焉能得知《论衡》?事实上,魏文帝之“文气说”,才真正开启了以才性论述诗文的先河。《典论·论文》曰:“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。……至于引气不齐,巧拙有素,虽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。”这与《非草书》“书之好丑,在心与手,可强为哉?”甚为相似。赵壹虽早于文帝,但所谓的《非草书》是在文帝之后六百余年的唐代才出现,不可执后而议前。
文帝之后,刘劭《人物志》以气血筋骨对应五行来论述人的操行才性,以配合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推行,其成书大约在魏明帝时。正始玄学兴起,“才性”成为清谈主题。傅嘏、钟会、嵇康等论述才性离合,辨义析理,日趋精微。典午篡魏之后,清谈之风弥煽,由品评人物逐渐延及书绘文艺。《晋书·卫瓘传》:“论者谓瓘得伯英筋,靖得伯英肉。”东晋二王父子书法骨力之议,皆属此类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以“疏”“密”“缓”“捷”等术语评论诗词文赋,诸如“赵壹之辞赋,意繁而体疏”“仲宣捷而能密”等。明确以“迟”“速”概念论书者,实为梁武帝,其《草书状》云:“疾若惊蛇之失道,迟若渌水之徘徊。缓则鸦行,急则鹊厉。”论萧子云书曰:“笔力劲骏,心手相应,巧逾杜度,美过崔寔。”
由此可见,灵帝光和时期偏居西州汉阳的赵壹,不可能把中国文艺史上由魏晋之后逐步发展丰富起来的论书术语,皆能未卜先知,娴熟运用于《非草书》。由此也可推断《非草书》必非赵壹所作。
二、“故不及草”与“草本易而速”两者之间逻辑悖谬
《非草书》以“私书相与,庶独就书,云‘适迫遽,故不及草’。草本易而速,今反难而迟,失指多矣”为主要论据,批评当时学草之人违背作草之旨。看似气盛词严,实则大谬不然。只因作者将前后两个“草”字皆解作草书,遂致逻辑悖乱,文意不安。仅此一点,足以断定该文不出赵壹之手。既有文采又曾担任汉阳计吏的操觚之士,岂能不明“草”之多义?“草”字固然有草木、草书之义,但用为草稿、草拟之义尤多。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:“每为报书及赐,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”颜师古注曰“草谓为文之稿草”。《汉书·师丹传》:“丹使吏书奏,吏私写其草。”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:“嵩为人爱慎尽勤,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,皆手书毁草,不宣于外。”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:“时扶风马融在坐,为冀章草。”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:“(刘)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,并极其才思。”
凡古书中“视草”“草奏”“章草”“草章奏”“草成”“具草”“诏草”“进草”等皆为起草、草稿之意。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一直到《旧唐书》,此等史例不胜枚举。当然,“草”也有创造之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汉兴,萧何草律,亦著其法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:“汉氏诛除秦、项,未及下车,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。”至于“草”作为与篆隶等并列的书之一体,乃后起之义,于史籍虽不复少见,然多以“善草”“工草”行文,或径以草书称之,甚易理解。《后汉书·张超传》:“超又善于草书,妙绝时人。”《魏书·卢玄传》:“初,谌父志法钟繇书,传业累世,世有能名。至邈以上,兼善草迹。”
“草”之诸义,古人多能明了,赵壹也不例外。因此,把《非草书》归于赵壹,其谬亦甚。
三、“故不及草”只能解作“起草”
衣冠得体为延宾待客常仪,匆遽时无暇顾及礼仪,也属情理中事,所以史籍常有“衣不及带”“忙不及履”之词。《后汉书·王符传》:“(皇甫)规素闻符名,乃惊遽而起,衣不及带,屣履出迎。”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:“时(蔡)邕才学显著,贵重朝廷,常车骑填巷,宾客盈坐。闻粲在门,倒屣迎之。”“衣不及带”“倒屣”等,皆因匆遽所致,乃不得已也。这与古人私书相与,匆遽之时来不及草稿,难免词义不周,字体狼藉,显失敬谨之意,特言“故不及草”或“匆匆不暇草”,希冀对方见谅之理相同。
汉唐章表,字皆楷正,以示礼敬,此乃国典,一皆遵守。《史记·万石君传》:“(石建)为郎中令,书奏事。事下,建读之,曰:‘误书!马者与尾当五,今乃四,不足一。上谴死矣!’”即此可证史载“吏民上书,字或不正,辄举劾”不为虚言。草书难识,不施于章奏,古代一直如此,至少直到唐德宗时期是这样。虽间有例外者,然多为恩出制外,实属政治待遇,或事属特殊,牵涉军国大事。东汉显宗令驿马取北海敬王刘睦尺牍之草,魏文帝令侍中刘廙通草,东晋明帝特诏尚书令郗鉴草上表疏等,皆属此类。
“书疏尺牍,千里面目。”作字当以楷隶为敬,正如“整衣束带”晤面同一道理。但仓促之际来不及起草,下笔而成付与行人,也是常有的事。《梁书·伏挺传》载伏挺与仆射徐勉书,信末云:“近以蒲椠勿用,笺素多阙……须得善写,更请润诃。”由此可知,梁代士人书疏,依然经过“善写”之后才付与对方。到唐代也如此,尤其是上达天子的表疏,必须先草后写。《旧唐书·李繁传》:“及(李)泌殁,户部尚书裴延龄巧佞奉上,……(阳)城中正之士,尤忿嫉之。一日尽疏其过恶,欲密论奏,以繁故人子,为可亲信,遂示其疏草,兼请繁缮写。”《旧唐书·席豫传》:“豫与弟晋,俱以词藻见称。而豫性尤谨,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,未尝草书。谓人曰:‘不敬他人,是自不敬也’。”
明白这个道理,就能理解所谓“故不及草”,断然不指草书,何况其前尚有“适迫遽”三字,则只能是起草之义。
对“草”字的误解,从现有资料来看,其渊薮即是《四体书势》所谓张伯英“匆匆不暇草”及《非草书》中的“故不及草”。唐代蔡希综《法书论》关于“匆匆不暇草书”的谬解一出,承其误者历代有之。黄庭坚说,“拔忙作草,殊不工。古人云:‘匆匆不暇草’,端不虚语”。黄氏学究天人,于此不免失之。明人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:“古人云:‘事忙不及草书’。尝举以戏草草者,其人辄妄对曰:‘章草固不易作’,此尤可笑。”张氏或许明了“忙不及草”之义。清代孙承泽《庚子销夏记》:“书家草法,宜入规应矩,力能扼腕,处处停笔为佳,所谓忙中不及草也。”赵翼《陔餘叢考》:“草书乃最速者,反云不暇。东坡尝求其说而不得。近代虞虹升以为草书乃起草耳。不暇草书,谓不及起草,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,失敬谨之意,故言及之。此说甚新,然亦非也。……是以作草甚难,而匆遽时有不暇也。”
虞虹升之解释完全正确,但依然有人承袭赵翼之误。《中国书法史》云:“不轻易下笔,下笔必要成为楷式传与后世,……意思是急遽没有充裕的时间来作草书。”辛德勇认为张芝所言乃是一种自谦,为自己行文“简慢”表述歉意。但支吾其词,未能明言“草”为何义。
四、“上比下方”之词与汉晋士风
后汉士人多以天下为己任,放言高谈,亦以道德节操立论,“尊崇节义,敦厉名实……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,三代以下风俗之美,无尚于东京者。”桓、灵之时,以书绘之技高自标置的事例极鲜。蔡邕于熹平六年(177)上书灵帝,直陈“书画辞赋,才之小者”。杨赐在光和元年(178)建议灵帝,远斥鸿都门下“虫篆小技”之徒。大约生于光和二年的曹魏大臣刘廙,其对草书的认识态度,颇可代表汉魏士大夫,借此亦可管窥草书在当时的地位功用。《三国志·刘廙传》:“文帝器之,命廙通草书。廙答书曰:‘初以尊卑有踰,礼之常分也……必如严命……何敢以辞’?”一个“器”字,说明草上表疏,一如“剑履上殿”“赞拜不名”一样,乃出恩宠,与书之优劣大略无涉。一个“礼”字,则又可证草书上表关乎国之典章制度。
汉末士风决定了张芝不会炫耀末技,其家世遭遇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自我矜伐。张奂原籍敦煌渊泉,先后遭两次党锢,因平定西羌有功,放弃赐钱除郎之赏,以换取徙籍弘农违制之恩。面对“锢及五属”的党禁,张芝岂可矜夸以自招祸端?
曹魏正始开始,社会风气改变,自我标榜陋俗蔓延,上至帝王为政、士大夫清谈,下至书绘乃至博弈,皆有体现。史载晋武帝问王济,其叔父王湛何如人也?王济因称其美。帝曰:“谁比?”济曰:“山涛以下,魏舒以上。”时人谓湛“上方山涛不足,下比魏舒有余”。此话与世传张伯英“上比杜、崔不足,下方罗、赵有余”何其相似乃尔!到底是张芝矜夸之辞影响了百年后“朝寡纯德”之晋人,还是“耻尚失所”的晋人以浮诞时风来臆度百年前的张芝?识者自能分辨。《南史·张融传》:“融善草书,常自美其能。帝曰:‘卿书殊有骨力,但恨无二王法。’答曰:‘非恨臣无二王法,亦恨二王无臣法’。”由此可见。以书绘相高之风,实乃晋宋齐梁时事,并非东汉桓灵时期风俗。况且,最为值得注意的是,“上比下方”说辞,最早均见于晋人著述,主要有卫恒《四体书势》、荀勖《文章叙录》及挚虞《三辅决录注》。《四体书势》云:弘农张伯英者,因而转精其巧……伯英弟文舒者,次伯英。又有姜孟颖、梁孔达,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,皆伯英弟子,有名于世,然殊不及文舒也。罗叔景、赵元嗣者,与伯英并时,见称于西州,而矜巧自与,众颇惑之。故英自称“上比崔、杜不足,下方罗、赵有余”。
《四体书势》全文,其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,所涉人物皆直呼其名,符合“名以正体”之意,而论草一节中张伯英等人,却一律字而不名。这种有乖主体行文的称谓,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,那就是:论述张伯英的文字,十之八九不是出自卫恒之手。崔瑗、蔡邕天下名士,尤其是蔡邕,与张芝同时,且班秩尊崇,卫恒行文尚且不讳。张伯英及所谓的姜、梁、罗、赵等,彼皆匹夫,何德何能,竟得字而不名?当是卫恒遭祸之后,该节文稿经他人篡改或续补。此外,姜、梁、罗、赵及田彦和这五人中,前四人之名,皆可见于后来的论书之作,唯独田彦和不见对应之名,即此可知此人名字相同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认为“名字相同,起于晋、宋之间,至唐时尤多”,并列举史例予以佐证。如果顾氏所言不差,则这一条也可助证卫作遭人篡改。
刘知几批评《晋书》编撰不重史料甄别去 取,《旧唐书》直斥“好采诡谬碎事,以广异闻”。卫恒遭祸,中断了对汲郡竹书的考正,后由束皙续成。卫有《古来能书人录》一卷,也遭刘宋虞龢擅改。结合卫恒遭遇及其论草人物称谓,则可推知《四体书势》关于张伯英的“诡谬碎事”,当是他人之词。
《文章叙录》虽冠名荀勖,乃谓首领其事而已,不能简单推定该录完成于太康十年荀勖卒前。《晋书》本传载其“既掌乐事,又修律吕,并行于世”。如果执此以据,则似乎荀在生前即已全部完成了律吕的修订。实则不然,其所治钟罄,后由其子荀籓续作。本传又载,“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,诏勖撰次之,以为《中经》,列在秘书。”然则荀于生前并未完成《中经》,有《晋书·王接传》所载卫恒、束皙之事可证。荀于太康三年由中书监改任守尚书令,职务之变动,也必然会影响到典籍整理的进度。综合上述各种因素,可以推断《文章叙录》的最终完成,当为荀勖身后之事。果真如此,则卫恒因祸而文稿遭人篡改后收入《文章叙录》,就是情理中事。
《三辅决录》属史传性质,赵岐“恐时人不尽其意,故其书唯示同郡严象”。由此可 断,《决录》于赵岐身前不行于世,挚虞注后方得流传。其注赵袭云:“岐从兄袭字元嗣。先是,杜伯度、崔子玉以工草书称于前代,袭与罗晖拙书,见嗤于张伯英。英颇自矜高,与朱赐书云:‘上比崔、杜不足,下方罗、赵有余也’。”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引《三辅决录注》:“赵袭,燉煌太守。”此说有误。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:“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,行至襄武……贼欲胁以为帅,岐诡辞得免,展转还长安。”可见敦煌太守乃赵岐,且未就任,与赵袭无关。且赵岐本传明言,赵氏一门遭祸,唯岐及从侄赵戬逃生,余皆罹难。
综上所述,“上比下方”之流传,挚虞之误在先,其后挚说窜入卫恒《四体书势》,最终被《文章叙录》收录。后之好事者不考挚虞之误,遂托名赵壹而作《非草书》,以达其私意而已。范书问世后,齐梁之士多有悉知赵壹者。《南史·卞彬传》:“彬险拔有才,而与物多忤……乃拟赵壹《穷鸟》为《枯鱼赋》以喻意。后为南康郡丞……仕既不遂,乃著《蚤虱》《蜗虫》《虾蟆》等赋,皆大有指斥。”卞氏本传于此所载颇详。
《非草书》末一段,有“稽历协律,推步期程。探赜钩深,幽赞神明”之语,貌似与“道术”有关,实乃作伪者为照应“有道张君”而故为此说。看似天衣无缝,实则显其无识。汉末儒士,视谶纬为敌,正如范晔所言:“是以通儒硕生,忿其奸妄不经,奏议慷慨,以为宜见藏摈。”刺世疾邪之赵壹,岂能以阴阳术数谶纬图书为他人指点迷津?与此相反,倒是在宋齐之时,图谶符应之说尤为流行。
通过以上辨析,可知张怀瓘《书断》所言贬草之论,断不可信其所指为 东汉赵壹。《法书要录》所辑书论间有伪作。盖因张彦远为唐人,且该书保存不少中唐之前书论,故后人多信而不疑,不加悉心考辨,遂尔雷同一声,认为《非草书》乃东汉赵壹之文。然文本乖谬错乱,足以自证其伪。今不揣浅陋,以申鄙见,祈通人指正。
(原文见《书法导报》,本报转载有删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