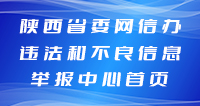大医吴鸣琰
来源:榆林日报 时间:2024-09-12 08:32:36 编辑:李小龙 校对:张倩 责编:王丹
吴鸣琰,这个名字我在神木中学上学时就听说了,神木城里的同学也经常说起他各种各样治病救人的故事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吴鸣琰在神木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我从穷乡僻壤的高念文村走到神木城,古老的城墙、高大的城门、熙来攘往的街道、琳琅满目的百货公司着实让我开了眼界,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住在城里的那一个个传奇人物。能把要死的人救活的吴鸣琰,一把草药治百病的张政泰,上课只带一只粉笔的徐存厚,博古通今的杨和春,会教书、会写文章、会照相的武绍文,会设计制造机器的李祝捷,能把石头变成玻璃的郑文龙等等,是这些人让我对科学技术由抽象变成具体。
1981年,神木南关小学发生了一件全城妇孺兼知的大事,一位老师在校园乒乓球台边训斥学生,以手势助语气,手指戳到学生的脑门,学生脑袋向后一仰,恰巧碰在了水泥乒乓球案子的尖角上,当即头上血流如注,人像气球放了气,软倒在地。送到医院一检查,颅内出血,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,否则危在旦夕。吴鸣琰在县医院简陋的石头窑洞手术做了五六个小时,孩子得救了,浑身湿透的吴大夫软倒在地。这场手术不仅救了这个孩子,更救了闯祸的老师,救了两个家庭。
一个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,靠的是他所创造的一个个奇迹。
1988年2月12日,我大女儿出生,也是我们一家与吴鸣琰结缘的日子。这天傍晚,我们与已经担任神木县医院院长的吴鸣琰经历了生死攸关的十分钟。
那天下午五点,女儿在县医院出生了,可胎衣一直下不来,剥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,年轻的大夫头上渗出的汗珠闪闪发光,脸憋得通红。刚刚经历生产的妻子恐惧又痛苦,把头深深埋在我的腋下,双手死死地拽着我的胳膊。
“你快去叫吴院长吧。”大夫对我说,他的声音很低,可我听了不啻平地惊雷。我不知道胎衣下不来的后果,但我知道不是人命关天,不会让叫吴院长。顾不上多想,我骑车直奔吴院长家。好在吴院长就住在医院旁边的旅社大门口,离医院不到五百米。吴院长正挽着袖子和面,准备做晚饭。我见到他只会重复一句话:胎衣下不来四十多分钟了,胎衣下不来四十多分钟了!把吴院长的手从面盆里拽出来,哀求快去救人,腿软着就要跪下。
吴院长连忙扶着我说:“小伙子,不要着急,我马上就去。”当即叫他的女儿吴月萍先去做手术准备,他洗洗手就来。他的女儿也是医院的护士,当吴院长到病房时,她已经打亮无影灯,准备好必要的器械。吴院长一到就开始上手剥离,只听他说:“哎呀,粘的挺厉害!”
终于剥离成功了!整个病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剥离过程不到两分钟,但我却像是经历了一生。剥离完成后,吴院长弯下身,轻轻地用卫生纸把妻子身上的血污、床上的血污一遍遍地细细擦拭,擦拭过程中我才看清穿着白大褂的吴院长个头不高,身体瘦瘦的,说话声音低,动作很利落。吴院长嘱咐:“出血太多,一定要输血。”
吴鸣琰,这个名字从此珍藏在我的心里,永远忘不了那双被我从面盆里拽出来沾满面粉的手,永远忘不了他弯下腰轻轻地为我爱人擦拭身体、擦拭病床的动作,永远忘不了他走出病房走在医院院子里灯光下那洁白温暖的背影。
2021年,我的女儿在上海的妇产医院生孩子的时候,我不由得又想起她出生时那个惊心动魄的傍晚,想起那个个头不高、身穿白大褂、说话声音柔和、医术高超、被神木人奉为“神医”的吴鸣琰。
2023年春节,我和妻子回到神木老家,正月的时候我和妻子说:“咱俩去看看吴院长。”妻子说:“没有联系方式,不知道住处,怎么找到他?”我说:“在神木找一个曾经当过官的,可能费劲。找吴院长,一定好找。”
凭着对吴院长旧家有点印象,在神木老城南关的斜街停下车,见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,向他打听吴院长的家,他果然知道,而且热心地掉头带我们去。到了吴院长家,大门紧锁,临街的诊所也关闭了。街对面坐着几个老头聊天,向他们打听,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,吴院长九十岁了,老了,不能开诊所治病了,在旧县医院门口政府奖励给他的房子里住,有保姆伺候着。
根据几位老人的指引,我们很快找到了吴院长在旧县医院门口的家。听说来了客人,在客厅小床上躺着的吴院长赶紧穿好衣服坐了起来。
吴院长确实是老了,白头发稀稀疏疏,原本大大的眼睛,现在眼袋快把眼睛都挤没了,小小的身躯陷在床铺里,俨然一个小老头。显然他不认识我们,眯缝着眼睛疑惑地盯着我们看。我告诉他我是谁谁的儿子,他马上说:“你们家是在花石崖高念文村。”父亲是神木的老干部,又是吴院长的同龄人,过去他们熟悉。
“你们村我去过,任念功村我也去过。”
“我们村那么偏僻您都去过?”
“比你们村偏僻的地方我都去过,神木县所有的乡镇我都去过,四千多个自然村,至少一半去过。”
“我1953年来到神木县医院,1993年退休,医院工作四十年。退休后自己开诊所二十年。治疗病人超过十万,手术病人一万多。”九十高龄的吴老,说话声音低,但表达特别清晰。原想见见他就走,看他精神状态如此好,我特别想和这位老人多聊聊。
“您治疗过的病人印象最深的是谁?”潜意识里,我想听吴院长亲自讲讲这个轰动一时的开颅手术。
吴院长缓缓地说:“那可说不完,我刚来神木的时候,神木是一个偏僻落后,缺吃少穿、缺医少药的地方,老百姓的日子特别苦。1962年夏天,阳崖村一个姓雷的老汉背来他的老婆,老婆背患‘蜂窝组织炎’,化脓恶肿,如不住院做手术,生命危在旦夕。可是雷老汉穷,交不起住院费,准备带老婆回去等死。我冒着极大的风险,在门诊处置室,直接进行坏死组织切除,整整一个小时,不全麻,不输血,相当于刮骨疗毒。手术过程,我的口罩、白大褂溅满脓血,切除的坏死组织堆满方盘,病人痛苦,医生更痛苦,没办法,救命要紧。”
有一件事,吴老说他印象很深。1959年的冬天,临下班,医院的领导交给他一个紧急出诊任务,说栏杆堡有一个产妇产后胎衣滞留有二十多个小时了,生命危在旦夕,要求他连夜去栏杆堡。栏杆堡距县城有三十公里,步走要近六个小时,走路辛苦他不怕,他怕狼。那时候去栏杆堡的路不仅荒凉,还要路过一段原始树林。听人说,狼咬人首先是咬脖子,他就把围巾一道一道缠在脖子上,最后挽了一个死疙瘩。手里拿了一根打狗棍就上路了。到了地方,围巾都湿透了。来不及喘口气,在简易的土炕上就开始人工剥离,顺利救下了年轻的产妇,母子平安。
听吴院长讲一个个他与病人的故事,我产生了一个疑问:“吴院长,您究竟属于什么科的大夫?”
“病人得什么病,我就是什么科。”说完这句话他“嘿嘿”地笑了,像一个可爱的小孩。“从陕西省卫校毕业分配到神木后,我1956年、1960年、1972年先后三次到西安进修过大内科、传染、胸外、脑外、腹腔外科,还进修过中医。先干后学,边干边学。”
吴院长说刚到神木的第二年,那是1954年,他到贺家川下乡,春节了,他也没有回县城里的单位,那里也是一个人。回长安老家更不可能,来去路上就要半个月。过年当地人都回家了,就他和看门的老头一起过年。正月初三,县里下来一个部门领导,看到竟然有一个县医院的医生在这里过年,这个医生还是个外地小青年。过年还在这里下乡,就让人给这个小医生单独做了一碗羊肉饺子。吴院长说,那是他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饺子,特别香!关中口音的“特别香”,好像格外加重了香的感觉。“特别香”重复了几遍,好像又吃到了七十年前的那碗饺子。他觉得不能自己一个人把这碗饺子吃掉,就礼让那位干部也吃,干部只尝了一个,谎称自己吃过了,不再吃。他坚持让干部再吃,两个人四只手把一碗饺子推来挡去,“蹦”得一声,居然把碗掰成两半,两个人对着撒了一桌子的饺子哈哈大笑。他一边讲,一边像个小孩子“嘿嘿”笑,眼睛眉毛都不见了,只剩下一张笑脸。收起笑脸,他说:“神木人对我是真好!”
聊天的间隙,我环顾他的小屋,是一个小小的二层,一层有二十多平方米,在一层客厅上二层的楼梯下摆了一张床,床边围着一张朱红色的旧办公桌,桌上放着他用钢笔写得一大本病案回忆。这一床一桌组成的空间就是吴院长躺下休息、坐起写作的地方。房间光线很暗,墙壁陈旧,家具也是七十年代最简易的那种。客厅的东墙上挂满各种奖状、旌旗,居中的一个镜框里张贴的是榆林地区卫生局1999年授予他的白求恩精神奖。
白求恩精神是什么?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。对,他是神木人民的白求恩。
高云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