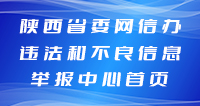如果比喻我是陕北旱风里的一株植物的话,我就是靠着信天游的营养长起来的。没有刻意模仿,也没有要以信天游为基础的创作目的,但当我走进“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,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”“三姓庄外沤麻坑,沤烂生铁沤不烂妹妹心”信天游的歌声里时,我完全沉醉在一种朴素、自然、简洁中了!
一次,我遇到了一位疯老婆儿。在乡上几个半老汉的鼓动下,她唱起了信天游:“向阳花开花朝南转,三回五回你怎不盘算?柿子下架枣子红,哥哥你不来我怎么舍!”“馍馍白糖就苦菜,口甜心苦你把良心坏;有朝一日天睁眼,小刀子戳你没深浅。”之后,这位有精神病的老人,便是我多年跟踪采访的主要对象,她唱的信天游实在太美了。“双手手我端起三盅盅酒,叫一声哥哥你不要羞回我的手”“细擀杂面油调汤,第一碗我双手手给你端上”“墙头上栽葱浇不上水,玻璃上吊线线亲不上嘴”……
至今,我一直还在搜集古老的信天游。在“有恨咬断七寸钉,为爱敢闯阎王府”的父老乡亲的爱憎里,热烈是:“手提上羊肉怀揣上糕,扑上性命也和哥哥交”;凄婉是:“九十月的狐子冰滩上卧,谁知道我的心难过”;思念是:“想你想得胳膊腕腕软,煮饺子下了些山药蛋”;率直是:“站在垴畔上望见天河水,忘了爹娘忘不了你”;爱是:“只要和你好上一回,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后悔”;情是:“双手搂住你的细腰腰,就像老绵羊疼羔羔”……情真,意切,信天游忧伤着他们的忧伤,信天游执著着他们的执著。
我用十年的时间写过一部长篇信天游叙事诗。我已老去了的青春,和这十年不无关系。但我错了,我闭门造车式的一遍遍地写、一回回地改,在远离生活的同时,也远离了信天游。这里,我真诚地感谢老诗人谷溪先生,他从书架上给我挑选了厚厚的一摞书——他全部的民歌书籍,还有叙事与抒情一体的经典长诗。两个月后,我读完了这些书,开始重新采访……终于进入了“老牛眼太阳当天上挂,吃一口干粮半口沙”“羊羔羔落地四蹄蹄刨,起鸡叫睡半夜不说熬”的艰苦创作中,也有了“贼来了不怕客来了怕,家里穷得光踏踏”“门栓栓抹点老麻子油,轻轻开来慢慢走”的生活。这部写我的乡亲们治沙造林的长篇信天游《红头巾飘过沙梁梁》,发在《延安文学》2000年第4期上时,我曾下决心再也不写出力不讨好的信天游了,可我发现自己像中毒似的经不住信天游的诱惑。我的诗,有无数属于善良的信天游……
在陕北,贫穷似乎是历史的根。翻开史册,陕北除自然原因的天灾,导致饥饿,导致反抗之外,再没有别的了。只有民歌像一疙瘩一疙瘩的金元宝,光彩熠熠。你可以说它是无奈的吼声,你也可以说它是爱情的绝唱,但无论怎么说,与一辈辈老去的人不同的是民歌活着,且活得那么年轻。一支歌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,抑或是一位水灵水灵的女子。他们背负着苦难,却欢乐地唱着,创造着辉煌的陕北民歌史。
我曾下决心不再写信天游了——“信天游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忧伤,一种旋律性的哭泣,有一种深度的杀伤力……我以为写信天游、唱信天游的人,一定会比别人少活上几年。”这是我写 在长篇小说《信天游》里的话。不仅如此,信天游也太难写了,尤其是用信天游的形式,写一部反映改革开放陕北农村变化的叙事长诗!我却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方法,只有信天游!
在《金鸡沙》的创作中,我自始至终充满了激情。有时真是痛不欲生,一句词得用上几天琢磨;有时甚至想在地上打一阵滚儿,释放胸中的压抑。快乐当然也必不可少,在写下“一眼能化开黄河的冰,两眼看不透妹妹的心”的那个冬夜,我感觉到了一盆火在燃烧,并且一直燃烧到第二天,我还给从西安来的作家朋友诵读。不是说我写下了一句“经典”,我只是尝试着为传统信天游的创作拓展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。信天游需要创新,任何一个不具备创新的艺术,必将会在历史的发展中死去——信天游太需要创新了!从李季的长篇信天游叙事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之后,有学者就说信天游从此死了!其间无论是纯粹的信天游写作,还是信天游的杂交体,几乎都被读者很快忘记。当然,《金鸡沙》没有走出传统信天游的模式,我只是倾心于让传统的信天游更加优美,比如“山桃儿开花九卷卷,你妈妈生你花眼眼。”后一句人人皆知,我只是在比兴上让两句更为和谐,尽管“吟”了好长的时间,我却很是激动了一番……
“对对蝴蝶对对飞,对对花朵儿亲嘴嘴。
对对柜子对对箱,对对凳子成一个双。
对对穿衣镜柜上摆,就是等不到妹妹来。
对对唢呐对对号,哥哥我一个单爪爪。”
而在写《金鸡沙》的过程中,如何使信天游在“赋比兴”里更为流动、洒脱,也是我始终的努力与坚持。
这里,我还想说“诗经”的信天游,“乐府”的信天游,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的信天游,我不敢期望那些视民歌为下脚料的诗人们唱民歌,但我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,能关注朴实无华的信天游,能关注与自然和谐的信天游,同时关注信天游的创作与研究,使信天游能真正登上我们民族文学的大雅之堂。
多年前,在老家金鸡沙,坐在母亲的热炕头,突来灵感,我写下这么两句诗:有一个荒凉叫毛乌素沙漠,有一个不安叫无定河。后来,这首写陕北之北的诗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等报刊上,现在想起这一切,都是那么的美好!因为,毛乌素和无定河加起来就是我老家的村庄——金鸡沙。
金鸡沙有千百万粒沙子,每一粒我似乎都数得清清楚楚。在金鸡沙我能获得最真实的方向感,村子的西边是无定河,北边是毛乌素沙漠,东边一户人家的小孩每天夜里哭,我种在南边的庄稼在一天一天长大。在金鸡沙我获得真实方向感的同时,也清晰地获得了我作为人的尺寸。是的,这就是我的村庄,我老家的村庄。
这是我的村庄,草木生长的季节,人淹没在庄稼和草里,哪天起风,就叫风吹草底见牛羊。夜里有人在炕上咳嗽两声,一个村庄的狗都会跟着叫上半夜。一盘大土炕占据半个房间,村庄里的汉子晚上往炕上一躺,呼噜声里女人才睡得踏实睡得香。
这是我的村庄,我在这村庄里花了很多年长成大人,长得与一根玉米秆子差不多高。现在,我想再花多少年的时间,把自己往小里长。我的一生都属于这个村庄,最后小得跟村庄里的一粒沙子一样,甚至比沙子更小,这不光是由于我一毫米一毫米地把这村庄爱了个遍,还由于我也被这村庄一毫米一毫米地爱了个遍。
这是我的村庄,它由土地和父老乡亲的脚印、炊烟和信天游组成。在村庄的每一寸土地上,脚印好像一枚枚随意而亲切的邮戳,盖在村庄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上,五谷丰登的祈盼是全部的内容,乘着风调雨顺的特快专递邮船,驶向大红灯笼高挂的年……在这村庄的土地上,我来来回回地走了太多次太多次。
多少年来,我在村庄的土地上种下过玉米、土豆、糜谷,也种下我的儿子,我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得和荞麦差不多高,长得和糜谷差不多高,看着他和一根玉米秆子差不多高——高兴地看着儿子和我是一个模样,儿子也是我种下的最后一茬庄稼。我爱这片土地,像爱我的庄稼从根部往上面的叶子里爱,像爱我的儿子从骨头里往皮肤外面一点一点地爱,细致入微地爱,仔仔细细地爱。
金鸡沙,在我的村庄里,我的爱就这样在成倍增长,被浓缩,被拉长,被放大:
“锣鼓声震天鞭炮声响,
勾一盘五谷灯感谢党。
高粱灯红楞楞谷子灯黄灿灿,
麦子灯尖又尖豌豆灯圆又圆。
麻子灯绿来太平灯亮,
十二盏生肖灯照四方。”
一声信天游,一年又过去了。昨夜的梦里,金鸡沙的庄稼,真的长得像我诗里写的一样。
霍竹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