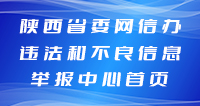“像牛一样劳动,像土地一样奉献。”我又一次站在路遥的墓碑前,看着铭刻在墓碑上他说过的这句话,无法抑制的眼泪,扑簌簌地流了出来。
路遥的生命,或许就是为了文学而存在的。听他说过,在七八岁时,因为家里穷,父亲把他带到几百里外,过继给了他的伯父。当时说是来玩的,几天就回去,可父亲却在来日清晨,撂下他一个人悄悄地走了。尽管路遥那时还小,但他敏感的心已有察觉,他不想让父亲难堪,悄悄跟了一段路,出了村子,躲在一棵大树的背后,目送着父亲走远。路遥深情地记录了这次经历,说他真想大喊一声,跑过去,抓住父亲的腰带,死活跟着父亲回家去。但他控制住了自己,任凭眼泪唰唰地往下流。他知道,伯父虽说也老实,也贫穷,但还咬牙能够勉强供他读书。这就非常好了,年幼的路遥,把能读书上学看得重于一切。
这是路遥的智慧。
坦率地说,我能走上文学之路,是路遥的《人生》带着我走来的。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在扶风县农机局以农代干打发着日子。现在很少有人理解“以农代干”这样的名词了,如果读了路遥的《人生》,认识了《人生》里的高加林,知道了他的特殊身份,大概就能知道以农代干的意思。也就是说,我虽然身在机关做着干部的工作,吃的却是农业粮,是要把生产队分配给我的粮食,按照合同约定,缴售到辖区粮店,拿着粮店的收购清单,再到工作的单位,由分管后勤工作的人按合同从县粮食局等量兑取粮票,我才可以在工作单位吃到食堂的供应。
刊发了《人生》的《收获》杂志,就在这个时候捧在了我的手上。是夜,我卧床看了一个开头,就再也放不下,一口气读到深夜三时多,读完后,翻过来,对其中的一些章节又重读了一遍。我读得泪流满面,为高加林,为刘巧珍,也为黄亚萍,在我的意识里,觉得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就是我,他的理想和追求,他的命运和生活,几乎就是照着我当时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来写的。
合上杂志,我闭上眼睛,却还管不住热喷喷流出的眼泪……我从床上爬起来,坐在了一张简陋的三斗桌前,认真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。
到今天,缅怀路遥,我最为感动的,是他影响了我,引领我无怨无悔地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其实要说,不只是我,那一代如我一样的青年,谁没有受路遥的影响?谁没有被路遥所引领?他的成名作《人生》,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,成为影响和引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度。
记得几年前的一个腊月天,我和几位文学界的朋友受邀去陕北的志丹县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轮到我作报告时,选题自然地定在了路遥和他的作品上,我给大家说,我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,说不出别的话,但我愿意和大家重读《人生》。
重读《人生》,从哪儿读起呢?
我不知别人会怎么说,但在我阅读了路遥的全部作品后,我想我们从他的随笔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来读,也许更能读得懂路遥,也许更能够读得透《人生》。
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是一个阅读路遥和《人生》的通道,从此能够真切地穿透他的作品,从而进入他的内心世界,清晰地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,以及创作过程的艰辛,正所谓“字字看来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”。是的,他的追求与成功,他的忧思与矛盾,都深深地渗浸着传统文化的汁液,这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的生命必然,他因此受益匪浅,成为创作时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。他立足于此,又放眼世界文化,广纳博取,把鲁迅,把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等大家名篇百读不厌,使他的创作境界宏阔而高远,又意韵深长。
奠定了路遥创作基础的《人生》,应该是他生命和生活背景的必然产物。他年轻的生命,就曾不停地奔波在“城乡交叉地带”,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,对于身处封闭贫困农村的他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,是物质上的,更是精神上的。路遥痛苦地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,于是在有可能破除旧的框架、产生新的机遇时刻,他敏锐地突入进去,用他的笔,形象生动地为苦闷着的农村青年推出了一个独具典型意义的人物。
这个人物就是高加林。他身上具有了现代青年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自信和坚毅,同时又保持着质朴和勤劳的传统美德。他心性极高,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。当生活给了他可能大显身手的机会时,他即投入了极大的热情,努力工作,力图有所作为。在此之前,村子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,让他无奈而苦恼,甚至有些绝望,恰在其时,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。这使失意之极的高加林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。突然地,高加林的生活发生了变化,他走进了理想中的城市。在这里,他又遇到曾是同学的城市姑娘黄亚萍。与巧珍相比,黄亚萍的洋气以及开朗活泼、大胆炽热,自然使高加林的情感发生了倾斜,慢慢地接受了黄亚萍的爱。
好梦总是难圆。高加林被人告发了,他只得再次回到农村。
《人生》之后,路遥开始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创作。这部史诗般的鸿篇巨制中,路遥一口气写了100多个各具时代特色的人物群像,其中孙少安、孙少平两兄弟,是路遥所要着意刻画的,在他们俩身上,依然有着高加林挥之不去的影子。因此,在我看来,《平凡的世界》是路遥成名作《人生》的一个延续和拓展。所以说,我们重读《人生》,是要把《平凡的世界》联系起来一块儿读的。每一个人读了,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体悟,但我认为,入木三分地写出生活和苦难、残酷的卑微,绝对是路遥文学实践的一个特色。或许,一位作家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,但要像路遥那样,在创作中不至于陷入平庸沉闷和种种不如意的泥沼,神奇地转化成高尚闪光的艺术品,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直到今天,我还想再次提出重读《人生》。我不断地重读《人生》,让我更加坚实了过去对于路遥的认识,他这样诗意的创作态度,牢固地树起了他作品的美感特质,并影响着我……
1986年的夏天,我因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渭河五女》,被县上安排在文化馆搞群众文化辅导工作。路遥在这一年完成了他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创作,《花城》杂志的主编亲自来陕西约稿,想要去凤翔县参观考古开挖的秦公大墓。此前一天,路遥给我打来电话,车过扶风,还想去扶风县境的法门寺走走。我答应了路遥,来日在县文化馆等到了路遥。他的到来,使我喜出望外。一路上,路遥对我说的,都是鼓励和关心的话,并且特别嘱咐我,要注意身体。他是用柳青的话来嘱咐我的:文学是以六十年为单元来计算的。
因为有我在扶风县接待路遥的经历,他和我在此后的日子里,多了一些往来,我常有来西安城办事的机会,幸运地碰到了他两次。与别人碰到了也就碰到了,打一声招呼,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,就过去了。但与他碰见了,他常热情邀我去他的家里,坐一坐,说说话,吃一顿饭……我们一起在他家里包饺子,吃饺子,其乐融融,快活不已。
数年时间过去,我从扶风县文化馆先是入西北大学读研,后去咸阳报社,再调到西安日报社工作,我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,到手的活儿,还有眼前的活儿,几乎与文学不搭界。但我依然留心着文学圈子里的事情。突然从报社跑文艺的记者口里听说了路遥的健康问题,让我吃惊不小。不过我没想到问题会那么严重,直到路遥的弟弟、我的同学王天乐寻到我的办公室,说他哥在病床上念叨我,我便二话不说,去了路遥住院的第四军医大学,拜见了他。短短十来分钟的见面,是他主治医生对我的要求,我俩没有机会多说什么,我拉着他的手,他拉着我的手,他告诉我,他想喝一碗钱钱饭,我便尽快想办法满足他的心愿,他还让我猜他生来最钦佩的人是谁?我们像过去一样,惺惺相惜。只是我没想到,这次拜见竟是永诀!
呜呼哀哉!我心里永生着的路遥啊!
吴克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