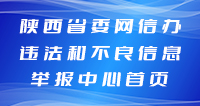春天里的事
来源:榆林日报 时间:2025-04-08 08:53:08 编辑:李小龙 校对:李娜 责编:王丹
三月,一场雨后,无风,有云,人心静。我立于阳台,开了窗,雨水、尘土、草木或者也掺杂了一些城市建筑的气味儿,一齐涌入鼻腔。嗅了再嗅,这气息,也熟悉,也陌生,继而翻搅出我陈旧记忆中发生在春天里的往事:关于农耕和其他,关于找食野味。
小时候,我们住在乡村。在村庄,冰河消融了是春,土地松动了是春,柳树发芽了是春,桃花开了是春。当然了,若是爸爸将去年秋收后挂起的农具再一一拎起时,也可作为春天来临的证词。
春天的一场薄雨后,村庄像被雨水洗过一般,干净、明亮,散漫着独有的精气神儿。土院儿里湿漉漉的,

畔上的枣树上吸收着泥土和春雨给的养分,挂满了水珠,就像秋来树上长出的果一般。爸爸开了偏房的门,将去年秋收后收起来的犁铧、老镢、小镢、锄头、筢子、拿粪兜、绳,包括笸箩、簸箕或者小篓篓,通通清点一遍,哪样家什坏了或者钝了,赶紧翻出来修修补补或者列出清单重新置办。
一把被爸爸用惯了的老镢,休息了一整个冬季,镢把上落了一层灰,铁刃上生出了一摊锈,看不出一丝烈、猛或是勇,相反看着呆呆的、钝钝的、木木的,但是爸爸并不会嫌弃它。那把老镢陪了爸爸多少年,我并不清楚,我只知道镢把的中部被爸爸的大手摩擦得光滑,还磨成了个细腰腰。镢头的铁刃上沾着铁锈,爸爸拿来一张砂纸,“刺啦刺啦”地擦着上面的斑斑锈迹。爸爸圪蹴在院里,一手抓着镢头,一手拿着砂纸,低着头,一言不发,不停地擦拭、打磨着那把镢头,一遍又一遍,直至它变得锃亮,变成了一把能被庄稼人庄重地扛在肩上的得力家什。爸爸不舍得撂下那把镢头,随着四季轮回,拾起它,收起它。也许,于爸爸而言,那镢头早已不是一件用于农耕的普通农具,它早已成了他生命甚至是身体的一部分。
早前,村里有一家铁匠铺,铁匠也是我们村的人,种地,也打铁。那时候,铁匠铺总能传出“叮叮当当”的铁锤敲打铁器的声音,邻里邻居家的剪子、刀子、镢头、锄头等生活用具和农用器具,大都是从那里敲出来的。铁匠没有徒弟,他是师,他的妻子是徒,夫妻二人你一锤我一锤,捶打出一个亮堂堂的光景。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流失,村庄寂寥了,土地荒了,农具也少被人扛起,自然,铁匠铺的炉灶也渐渐熄灭了。曾经的铁匠离开了村庄,到城里支起了做饭的炉灶,做起了餐饮,卖饸饹、抿节以及陕北人喜食的其他饭菜。铁匠支起的炉灶依旧透出火光,只是,他不再锻造坚硬的铁器。无论细碎的谷物种子,还是坚硬的铁,抑或柔和的面,都在铁匠的手中成了过光景的武器。是啊,人只要手持“武器”,就不会惧怕被砂石绊倒。
如今,生养过我的那个村庄,依旧还有乡亲们在春天等雨、在秋后收割,每一个节气都是他们在土地上实践出的谚语。在村庄,镢头不语,如爸爸一般的庄稼人不语,广阔无垠的大地也不语,他们一言不发地将农耕的秘密连同生命的题目埋进了土壤,等待雨生百谷。
一场春雨过后,山野里水津津、软塌塌,一团又一团的地软先于草木长出地表。黄土高原上的山多而阔,不管是阳坡还是背地,不管是荒山野坡还是河滩沟地,凡是被雨水滋润过的草丛中,都有可能会长出这一滑嫩嫩、亮闪闪的陆生藻类植物。有人说,地软是乡亲们的饕餮美食,它长于泥土之上,生于林草之间,低贱如尘埃,若是被人拾捡起则成美食,若是无人问津则又被自然的力量化为大地的一分子。因此,可以说,地软是大自然送给人们的野生美味,而居于乡下的人最能优先享用这一美食。
说起地软,想起小时候提着篮篮去山里捡拾地软的场景。一场小雨过后,天还灰蒙蒙的,妈妈就拿出大大小小的筐筐篮篮,准备上山捡地软了。上山前,妈妈早就在心里打好了算盘:哪一块地里可能有大而肥的地软,哪一块地里的地软可能已经被村里的哪个婶婶抢先捡走了,哪一块地里经常有羊群出没留下一摊又一摊的羊粪蛋蛋……哪儿能去,哪儿不能去,妈妈心里明镜似的。妈妈领料着我们,朝着她以为的好山头走去。到了目的地,果真如妈妈猜想的那般,拨开草丛,草根部一团又一团的地软卧在地皮上,像是早就开始等待我们来拾捡的黑精灵,颤着身子,进了我们的筐子。
捡回家的地软,被妈妈一股脑地倒在石床上,妈妈拿了盆子、筛子、袋子,还拿出一枚大号的针,针尖儿对着亮晶晶的地软一扎,地软便穿在针上了,大一点的杂草自然便被筛选掉落在地上。挑拣出的地软被放在了盆里,越来越多,越来越黑,越来越亮。被挑拣出的地软,又被妈妈倒进筛子里左右筛、前后摇、上下抖,细碎的土屑纷纷从筛子眼儿中逃出去。妈妈和我们越捡越起劲儿,一会儿的工夫,就将那堆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分离开来了。地软摊在石床上,妈妈用手指比画了一下,一半儿将做成地软包子,一半儿将做成家常小炒。
离开村庄后,我再也没有在一场春雨后捡拾过地软,甚至就没再见过这一陆生藻类植物。去年春天,一场小雨后,我们决定开车去山里捡地软。女儿吃过地软包子,可对地软来自哪里却是一无所知,她很是好奇。哪里有地软呢?我们对此毫无判断力。我们只知道,地软不会生在城市的街巷里,因此,我们的目的地是山,是一座更古、更老、更旧的山头。唯有在有风雨飘零、有草木生长、有鸟雀光临的山里,才是地软最合适的温床。最终,我们找到一片杏树林,树下杂草丛生,其间,藏着一片又一片黑亮亮的地软。女儿兴奋极了,她拿着一片地软,扑闪闪地抖动着。我想,她一定是知道了,她一定是知道了地软的来处。
看着女儿如此兴奋,我突然感慨,知晓了一个生物的来处,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种人生体验啊。
三月,小区里的花儿开了。有一天,女儿放学后,我用手捂住她的眼睛,牵着她,走向小区里一棵开满了粉色花瓣的桃树前。到了树底下,我松了手,女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当她的眼睛落在桃树上时,手舞足蹈起来。那一刻,花儿在绽放,站在花儿前的人也如花似叶,在热烈地绽放。
我想,春天该是一个长出生命或者见证生命的季节。
辛杰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