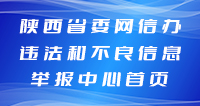屋前青杏转黄时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5-07-12 10:29:14
编辑:李小龙
校对:郝莉娜
责编:王丹
钢筋水泥的天地里四季流转得模糊不清,唯有老屋对面梯田里的两棵杏树,在时光里开着永不凋零的花。它们并肩而立,像两把钥匙,轻轻一转,便打开了童年那扇洒满阳光的木门。
那时家境贫寒,常常馒头咸菜就是一顿饭,肚子总像个调皮的娃娃,成天咕噜噜地叫。母亲说:“等梯田的杏子熟了就好了。”于是,盼着青杏转黄,成了我童年里最殷切的期待。
五月底,青杏还挂着绒毛时,我便开始踮起脚尖抚摸它。哥哥总说我傻,伸手刮我的鼻头:“小馋猫,还早着呢!”可我不听,每天放学都要绕到树下,摸摸杏子有没有长大一点,瞅瞅它们是否被虫子惦记。手掌蹭过圆滚的果实,摘下一颗咬一口,青涩酸的味道瞬间窜满嘴巴,不由赶紧眯起眼,收紧腮帮,等着它们钻入胃里。
终于挨到六月,蝉鸣声里,青杏开始泛出淡淡金黄。先是树梢的那几颗,像被阳光包裹,渐渐染上蜜糖色。接着,一串串黄杏便如灯笼般缀满枝头,在风里轻轻摇晃。熟透的杏子按耐不住,有的滚进沟壑,有的蹦向草丛,还有的干脆三三两两睡在凉荫中,等着人们捡拾和赞美。
黄杏吹响了冲锋号,我和哥哥拎着小箩筐,一个劲儿地往梯田杏树下跑。哥哥身手敏捷,腿脚一蹬便爬上树,蹲在粗壮的枝丫上,冲我喊:“接着!”成熟的杏子如雨点般洒落,我慌忙撩起衣摆,像只笨笨的小鸭子,咯咯笑着去接。杏子砸在头上,生疼生疼的,我也不舍得挪位置,还要仰起脸,看那满树的黄杏铺天盖地而来。
装满箩筐后,我们便在树下歇脚。我挑一颗最黄的,哥哥来一个最大的,裤腿上蹭蹭泥土,就开吃了。大陕北的土壤粗粝、松散,滤出的养分全化作杏肉里的绵甜,咬一口,酸溜溜、甜津津的汁液在舌尖炸开,仿佛心都要融化。最怕吃到虫子,有时吃得太急,“咔嗤”咬下半颗杏,突然看见果肉里有半条红虫子,吓得我“哇”地把杏扔出去,手指拼命蹭舌头,仿佛那半条虫还在嘴里蠕动。
父母则把挑回家的杏子去了核,晾晒在石床上,等着蒸发掉水分,变成美味可口的杏干。
后来,两棵梅杏的枝干上嫁接了李子杏,一到成熟季节,枝头挂满黄里透红的李子杏,个头大,汁水也多。我和哥哥连上学时都要用帆布书包带一些,和同学们课间分享着吃。过路的人们扛不住诱惑,偷偷摘几颗;劳作的人们没水喝,吃几颗解解馋。父母挑着一担一担的梅杏和李子杏到集市售卖,换来的钱补贴家用。
二十多年光阴转瞬即逝。如今,杏树早已化成了灶台下的一缕清烟。我也带着母亲离开了老屋,住进了城市的高楼大厦。可不知为何,我总会想起老屋对面梯田的那两棵杏树,想起在树下奔跑、摘杏的日子。那些在炎炎夏日里等待青杏转黄的时光,那些纯粹而简单的小幸福,总带着甜甜的香味儿,吸引着我跋山涉水地去回忆、去追寻。
馋虫作怪,周日早晨,我去超市买了一大袋子李子杏,可那看着水灵灵、黄澄澄的杏儿,飘着似儿时的清香,却再也唤不回儿时的场景了。
蝉鸣又起。我梦见哥哥爬树时划破了手臂,我接杏时摔了大屁蹲,还有那半条虫子的恐惧,母亲杏摊前明媚温暖的笑脸。醒来,我起身下楼,松土挖坑,在小树旁埋下一颗杏核。愿它冲破禁锢,向阳生长,结出这世间最鲜美、最动人的果实。
韩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