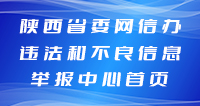那抹绿,是大地的脊梁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5-08-30 09:59:51
编辑:李 娜
校对:李强
责编:王丹
父亲的衣柜最深处,藏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上衣。袖口磨出了毛边,领口缝补过三次,却总被他熨烫得笔挺。每次翻找换季衣物时,他都会对着那件衣服发会儿呆,仿佛在回忆一段从未褪色的时光。
我最早关于绿色的记忆,是父亲脊梁的弧度。那时他总穿着这件军绿色上衣,清晨五点就蹲在院子里劈柴。斧头落下的瞬间,他后背的肌肉会绷紧,形成一道山梁似的曲线,阳光顺着衣领滑进去,在脊梁骨凸起的地方碎成金斑。母亲说,父亲年轻时总对着家里的穿衣镜练习敬礼,右手抬到耳边时,后背要挺得像门板,他说军人的脊梁是丈量国土的尺子,歪一分,脚下的土地就少一寸。
二十五岁那年,父亲终于收到了入伍通知书。他把通知书揣在怀里,在田埂上跑了三个来回,军绿色的憧憬在他眼里烧得发亮。出发前夜,他挑水装满了家里的三口大水瓮,腰都没弯一下。
可命运总爱给憧憬打个折扣。新兵训练第三个月,父亲在负重越野时突然咳出血来。军医拿着胸片叹气,说他的肺叶上有块顽固的阴影,像片长错地方的苔藓。“回家养着吧。”军官拍着他的肩膀,声音沉得像压了霜,“部队需要能扛枪的脊梁,更需要能站直的人。”
火车驶过戈壁滩时,他对着窗外倒退的胡杨林唱起了军歌,歌声高亢,直到那些枯瘦的树干变成天边的黑点。后来他总说,那一段的军营生活,像给骨头里注了钢,就算脱了军装,膝盖也不会随便打弯。
回到家乡的父亲,成了村里的护林员。他每天背着水壶巡山,军绿色上衣换成了深蓝色劳动布褂子,可走路的姿势没变——脚跟先落地,后背始终保持着微微后倾的角度,像被风刮过却不肯弯腰的松树。有一次暴雨冲垮了河上的桥,他带领着村民徒手挖排水沟,山洪漫过膝盖,他的脊梁却始终高于浑浊的水面。我哭着喊他回来,他回头时满脸泥浆,只露出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:“这山上的树,一棵都不能少,就像国境线上的界碑。”
去年冬天,我陪父亲去县城体检。拍胸片时,医生指着屏幕上那片模糊的阴影笑:“这肺叶长得真倔,这么多年硬是没再扩大。”父亲听完直乐,说当年在部队学过憋气,每次咳嗽时就想着哨所的旗杆,那玩意儿能在十级风里竖着,他的肺也能撑住。走出医院时,阳光正好,他忽然挺直后背,右手不自觉抬到耳边。那一刻,我忽然发现,他两鬓的白发里,还藏着当年军绿色的风。
如今父亲的脊梁已不再笔直,像被岁月压弯的扁担,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撑起一片天。邻居家的孩子半夜发烧,他背着孩子走了十里山路求医,后背弯成弓,脚步却稳如磐石;山洪冲毁河堤时,他第一个跳下去垒沙袋,浑浊的水没到胸口,脊梁却始终露在水面以上,像块不肯沉没的礁石。
那天整理旧物,我又翻出了那件军绿色上衣。试着穿在身上,衣摆盖住膝盖,袖口能塞进两个拳头,可当我挺直后背时,忽然懂得了父亲的执念。这抹绿从来不是简单的颜色,它是千万根挺直的脊梁织成的网,有的守在雪山哨所,有的立在乡间地头,有的藏在岁月深处,却都在用相同的姿态告诉世界:这片土地上,永远有不肯弯折的脊梁。
父亲不知何时站在身后,看着我身上的衣服,脸上忽然绽放出年轻的笑容。阳光穿过窗棂,在他鬓角的白霜与我胸前的旧布上,同时镀上了一层温暖的绿意。那抹绿,从来都在。
韩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