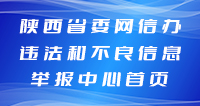大树小院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5-11-29 09:48:27
编辑:李 娜
校对:李强
责编:王丹
朋友皆知,我叫“大树”。这网名用了十几年,他们都叫我“大树(叔)”“大树哥”等。
当时取此名,心底或许藏着份自己都未察觉的期许——进入中年的我更加向往着树一样的沉稳与坚韧,根系深扎、枝叶伸展,能为人遮风挡雨,亦能独自面对风雨。几十年人生路,从青涩学子到乡村教师,再到机关干部,最后归于这方小院,我愈发觉得,自己终究是活成了大树的样子。
我的小院,距城里最繁华的街市,不过一步之遥。推土机的轰鸣似乎还在耳畔,高楼投下的影子几乎能触及我的屋檐。但就是这一步,宛若两个世界。门外,车马喧嚣,人声鼎沸;门内,则是我的“大树”之下,一方自在、安宁的天地。
推开八十年代镶嵌在斑驳墙壁上吱呀响的铁大门进到小院,院前的菜畦中有两棵已枯死的枣树成为木雕风景,自然而然想起鲁迅先生的“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还是枣树”,这树便有了文化内涵。青石板铺就的院子左右两边各放置一石桌、几个石凳凳,靠墙的地方放置了石槽,水龙头的水从石槽上哗哗流出,流进了菜地。边角旮旯很艺术地放置了石器、瓷器、木器等老物件。晨起锻炼身体后,必先在此沏一壶茶。茶叶不拘,有时是朋友寄来的明前龙井,清洌甘爽;有时是市集上淘来的老茶头,醇厚温和。水沸,冲泡,看茶叶在杯中舒展沉浮,如同审视过往岁月。什么都可以想,工作的得失、人情的冷暖;也可以什么都不想,让脑子空掉,只听鸟鸣,只看云过,喝茶发呆。这份“呆”,是前半生紧绷的弦,终于松弛下来的回音。从工作的那一天起,一刻不得闲,学生、教案、电话、文件、会议、下乡、下井、调研、人事、财务、上下关系、同事朋友等等,像无数双手推着我走。如今,时间终于是我自己的了,浪费得起,可静享这份奢侈的静谧。
这里是聊天会友的净土。来的多是在“减法生存”中、浪里淘沙下淘出来的挚友亲朋,无需客套寒暄。来一人,便对坐清谈,从鬼方文化的图腾考证,聊到某家老店的红烧肉火候;来三五人,则局面大开,有时为某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,有时又因一段趣闻哄堂大笑。院门一关,便将俗世纷扰与应酬隔绝于外。我恪守“四不要”中的“尽量不参加请吃和吃请”,但小院的茶永远为真朋友煮着,酒为好弟兄温着。这里的交谈,没有目的,不求结果,如风过疏林,自然而然,是精神上的吐故纳新。
这里是点对点旅行的出发地和旅途劳累后的栖息地。如今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行程,而是对未去过地方的专门打卡,有时将“旅游+非遗、旅游+篮球、旅游+美食、旅游+博物馆、旅游+鬼方文化”等紧密结合,欣然前往,这种点对点的旅行,是探索,更是与未曾谋面的景色和未知领域的一场深度对话。
这里是学习创作的工坊。屋内满架的书,是我这棵大树的根系。研究了大半辈子的鬼方文化,离岗后,终于有了时间来梳理、深钻。考古实物与资料、研究论文、地方志在不大的书桌上铺开,我像个老匠人,耐心地拼接历史的碎片。灵感枯竭时,便荷锄下地,去侍弄那几分菜畦。说来也怪,指尖触碰到湿润的泥土,看青椒又结了几个、番茄红了几分,那阻塞的思路竟也会豁然开朗。原来,文化研究与荷锄戴月,从来不是对立,而是相辅相成的滋养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交替,恰如大树的呼吸,一吐一纳,生命得以平衡。
这里更是亲情流淌的港湾。周末,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回来,小院便立刻沸腾起来。外孙子的各种神秘武器在各个“暗堡”隐蔽,外孙女在菜地里穿梭着逮那只飞来飞去的蝴蝶,他们的笑声比任何音乐都动听。妻女在厨房里忙碌,炊烟袅袅,饭菜的香气弥漫开来,那是一个家最踏实的气息。
当然,小院也并非全然避世。朋友家的婚丧嫁娶,请我当总管,我依然会郑重前往。我用多年协调组织的经验,依循古礼,观照现实,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办得庄重而妥帖。这让我觉得,自己这棵“大树”,依然能为需要的人投下一片阴凉,尽一些心力。
夜色下的院子,又是另一番韵味。月光如水,洒在石磨上,洒在菜叶上,万物都披上一层柔和的清辉。城里的霓虹在天边映出一抹微光,但小院里,只有星月和虫鸣。这一步之遥,隔出的是一片足以安放灵魂的净土,忽然想起苏轼那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回首“四要四不要”,它并非刻板的戒律,而是我这棵“大树”在人生秋季,为自己划定的生长边界。要做的,是汲取阳光雨露,让枝叶更繁茂;不要的,是修枝剪叶,避免养分的无谓流失。这是一种“退”的哲学,“退”回到生活本身,“退”回到文化根脉,“退”回到内心秩序。在这方小院里,我找到了后半生的节奏,不疾不徐,清风朗月。
贺世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