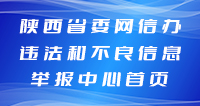榆林的冬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5-12-02 09:18:35
编辑:康敬卓
校对:张倩
责编:王丹
这儿的冬天,究竟是不问自来,也终究是有些脾气的。它不像南方的冬,那般忸怩,欲来还休的。这儿的冬,是扑面的,是彻骨的,是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、黄土高原上生养出来的执拗的。
你若想看它来的踪迹,不必看日历上的节气,只消看那风便是了。初时,那风还只是凉,拂在脸上,像情人别离时冰凉的手指,带着些微的、教人惆怅的温柔。可不知从哪一日清晨醒来,那风便陡然变了脸,从北边的毛乌素沙地,从无定河干涸的河床上,一路呼啸着刮过来。这风是糙的、利的,挟着细沙与干枯的草梗,打在窗纸上,沙沙地响,仿佛无数个不耐烦的指头在急切地敲着。街上的人也少了,即便有,也都是匆匆的。男人们将手深深地袖在棉袄里,脖颈缩着,像过冬的麻雀;婆姨们用头巾将头脸包得只露出两只眼,那眼里,也满是这风霜磨炼出的、坚韧而又淡然的光。
街边卖烤红薯的炉子,便成了最惹人爱的地方。那焦黑的炉膛里,透出暖暖的红光,一股子甜丝丝的、带着烟火气的香味,执拗地钻到冷风里,竟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来得诱人。买上一个,烫手地捧着,那热气便从掌心一丝丝地传到全身,仿佛将这整个冬天的严寒,都暂且隔绝在这小小的、滚烫的甜蜜之外了。
然而,陕北的冬,也并非一味地冷酷。若是遇上一场雪,那便是另一番光景了。这儿的雪,下得也颇有西北的性子,是爽快的,决不拖泥带水。起先,是零星的雪沫子,试探似的,随风乱舞。继而,便成了片片的鹅毛,密密地、斜斜地织成一幅巨大的白幕,将天地间一切都笼罩了进去。不过一夜的工夫,你推开门,便会“呀”地一声叫出来。那山,那川,那高低错落的窑洞屋顶,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,胖墩墩的,像个穿了大白棉袄的娃娃,憨态可掬。世界忽然间安静得出奇,往日里风的喧嚣、车的鸣响,都让这无边无涯的白给吸了去,化掉了。只剩下一种浩大而仁慈的静,让你不由得也屏住了呼吸,生怕惊扰了这天地间一场庄严的好梦。
夜里,若是雪停了,月亮出来,那景致便更奇了。清冽的月光洒在雪地上,并不像水,倒像是一层流动的水银,亮得晃眼。远处山峁的轮廓,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,柔和而又苍劲。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,也像是被冻住了似的,传不了多远便跌落下去。这时你若坐在暖炕上,守着通红的炉火,听窗外万籁俱寂,便会觉得这冬日的夜,虽然漫长,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、教人安心的味道。那是一种沉淀下来的、属于土地本身的温暖。
我常常想,这榆林的冬,怕是最能见出这方水土上人的品性。它不给你花红柳绿的幻梦,也不给你温吞水似的慰藉,它只将这风、这雪、这无遮无拦的酷寒,赤裸裸地摊开给你看。但也正因如此,那窑洞里炉火的暖,那碗里滚烫黄酒的醇,那亲人邻里围坐时一句朴拙问候的真,才显得那般可贵,那般扎实,足以抵挡窗外整个世界的风寒。
这么想着,耳畔的风似乎也不那么尖利了。它只是呼呼地吹着,像一首古老而苍凉的信天游,年复一年,唱着这片黄土地上,关于忍耐,关于希望,以及关于生命本身那顽强的、沉默的故事。
作者 薛澳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