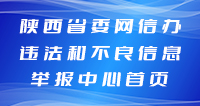数九寒天羊肉香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5-12-29 09:37:14
编辑:李 娜
校对:李强
责编:王丹
冬至日,陕北的天是清透的冷。不是那种潮乎乎的、黏在身上的冷,是干爽爽、脆生生的,像把一整块巨大的、没有杂质的冰悬在了黄土高原的上空。阳光倒是慷慨,明晃晃地铺下来,落在窑洞的窗棂上,落在院畔枯了的枣树枝上,落在泛着白碱的土路上,亮得晃眼,却没有一丝暖意,只把万物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,像用刀锋刻在地上似的。风从沟壑梁峁间闯过来,带着哨音,刮在脸上,起初是木,随后便是针扎一样的疼。这便是“数九”的开端了,老人们常说:“一九二九不出手。”手一伸出来,这干冷的风立刻就能给你染上一层糙红。
这样的天气里,人的心思便不由得往“吃食”上钻。仿佛只有那滚烫的、扎实的东西落进肚里,才能压住从脚底板漫上来的寒气。在陕北,冬至的头等大事,便是吃羊肉。这念头一起,仿佛鼻尖已经萦绕起那独特的、略带膻腥却又醇厚无比的香气了。
我起身,拢紧棉袄,往镇东头老韩的羊肉铺子走去。铺子就是个简单的泥坯房,门口挂着一只褪了毛的羊腔子,冻得硬邦邦,像一尊灰白的雕塑。门帘一掀,热气混杂着浓香扑面而来,瞬间糊住了眼镜片。屋里景象朦胧起来,只听得见大铁锅里“咕噜咕噜”的欢腾声。
老韩系着油亮的布围裙,正用一把阔背厚刀,剁着案板上的骨头。那声响结实、利落,“哐、哐、哐”,带着一种斩断寒冷的决绝。见我来,他抹一把额头的汗,笑道:“来啦?就晓得你今儿要寻这口。刚宰的羊,肥瘦正好,是吃沙葱、喝碱水长大的,肉味儿‘正’得很!”
这“正”字,是陕北人对羊肉的最高褒奖。不是饲料催肥的虚膘,而是羊儿在黄土坡上,一步步踏着日月,啃着带劲的草,慢慢积攒下的风味。那肉煮出来,香得扎实,膻得坦荡,带着土地与风沙的脾性。老韩舀一勺滚烫的、奶白色的原汤在粗瓷碗里,撒一撮碧绿的葱花,往我面前一墩:“先喝汤,驱驱寒气!”
双手捧住碗,那温度立刻从掌心蔓延到全身。吹开浮油,小心地啜一口。烫!一股热流直冲下去,所过之处,冰封的脏腑仿佛都舒展开了。汤是极鲜的,羊脂的润,骨髓的醇,都化在了里头。几口下肚,额角便沁出细密的汗珠,那逼人的寒气,似乎被这碗汤从里到外逼退了几分。
肉端上来,是大块的,连骨带筋,盛在厚重的陶盆里。肉炖得酥烂,用筷子轻轻一拨便脱了骨,颤巍巍的,浸满了汤汁。蘸一点用羊油泼过的辣子,送入口中,几乎不用咀嚼,那丰腴的肉香便在舌尖上化开。这味道,是直来直去的,没有江南菜式的婉转修饰,就像脚下这黄土高原,沟是沟,峁是峁,是什么样,就给你呈现什么样。吃着这样的羊肉,人不由得也变得实在、豁达起来。
我一边吃,一边和老韩闲话。他说,昨晚后半夜就开始忙活了,要赶在冬至这天,让乡邻们都吃上一口热乎肉。“咱这儿,天寒地冻的,一年到头辛苦。冬至起,夜就一天短似一天了。吃顿好的,肚子里有了油水,身上有了火力,才好扛过这漫长的九九天嘛。”他说话时,手里的活计不停,热气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凝成细小的水珠。
他的话,让我想起小时候。也是在这样寒冷的冬至,母亲天不亮就起来,在冰冷的灶房里忙碌。铁锅里的羊肉“咕嘟”着,香气弥漫整个窑洞,将玻璃窗上的冰花都熏得模糊了。我们几个孩子缩在被窝里,鼻翼翕动,贪婪地闻着那越来越浓的香味。等到肉烂汤浓,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上,父亲抿一口烧酒,我们啃着骨头,热气、香气、笑语声,将窗外呼啸的风雪彻底隔绝在外。
走出老韩的铺子,天色向晚。风依然冷硬,但我的周身却暖融融的,那股子暖意从胃里升腾起来,护着心口。回头望,铺子窗棂透出的昏黄灯光,在这青灰色的暮霭里,显得格外温存。
路上的行人少了,家家户户的烟囱里,都冒起了直直的、灰白的炊烟。我知道,在每一缕炊烟之下,大抵都有一锅沸腾的羊肉,都有一个被温暖着的冬至。这“数九”寒天的序幕,便由这一碗浓香四溢的羊肉,徐徐拉开了。它不华丽,却足够厚重,足以熨帖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熬冬人的心肠。
李宁